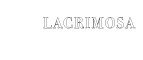1997年Stille采访
原文:Heavy oder was英文翻译 drachelein 2003
中文翻译 by Jun WK © 中文翻译版权归Jun WK所有,感谢Jun授权转载
译文初次发布时间: 1997年
如有任何形式转载和引用须联系译者
在最初的时候,Lacrimosa的主音Tilo Wolff是以Angst与Einsamkeit两张大碟吸引了黑潮爱好者注意的。Satura则预告了改变的来临,之后的歌特金属史诗Inferno则 在Lacrimosa的狂热者行列里增加了金属乐爱好者。现在,听众们正屏息等待新大碟Stille的发行。在这张大碟里,Lacrimosa完全地沉浸 在这仿佛是互相排斥的两种音乐元素中。一方面,精巧的古典乐结构仍被小心地保持着,另一方面,这张大碟里回响着有力的吉他riff。Stille用某种方 式列出了Lacrimosa以往作品的清单。乐队注意到了自己的局限,并且毫不掩饰这些局限。而且,他们甚至试图将它有机地融入音乐中去。 Q:你们的新大碟以Stille(寂静)命名。对于你而言,寂静指什么呢?
Tilo Wolff:Inferno(地狱)以Der Kelch des Lebens(生命的高脚杯)结束,对于Lacrimosa而言,一张大碟的第一首歌曲与前一张大碟的最后一首重叠、或者说相延续已经成了习惯。因 此,Der Kelch des Lebens是与Stille里的Der erste Tag(第一天)相联的,它再次重复了Inferno结束时的"我的梦想领着我前进,而我跟随它们进入了地狱"。它表现了某种情感:你似乎穿越了地狱的火 焰,然后终于,发现自己正站在山顶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凝视着脚下延伸到远方的土地,那是你试图触摸到的梦想的国度;迷雾消失了,你生命的新的一天展开了,你站在那里,让自己沉浸在冷静的观察 中。这种感情可以用平静的超然来描述,那是一种心灵的平衡,人们追寻着梦想穿越了地狱,然后终于在寂静中找到了它的某种状态。
Q:Stille的封面描绘了一个孤独的小丑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演奏的场景。这是你的一个噩梦的体现么?
Tilo Wolff:让我们不要那么文艺地解释这个封面的含义吧,这仅仅只是一个隐喻,或者说是一种象征。我们被人群包围着,我们能够觉察到他们的靠近与他们的表 现,我们拿这些作为我们行动的参考。当你准备好了一场表演,你假定有三分之二的人会来看。但是,突然你意识到只有在某个狭窄的范围里你才会感到愉悦,而这 就是你的身边空无一人。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害怕在没有人的大厅里演奏,更让我害怕的是被这种恐惧所构筑的那份情感。也就是说,当我突然发现自己在某种 层面上来说完全孤独了,我究竟该怎么办?我想倾诉却找不到任何人。严格地说,这种感情并不是由个体的孤单所引起的(关于个体孤单的主题,在 Lacrimosa过往的作品中已经表现过了),更多的是你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令人恐惧的现实所引起的。你原以为你可以可以掌控这个封闭的世 界,拥有它的一切。每天你都是这样子坚信着这一点,却最终发现自己的生活成了一堆碎片,比如说,你站在舞台上,面对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发现自己不得不将 一切从头来过。
Q:Lacrimosa的音乐不断地成长变化着,从最初的古典音乐到重金属元素。而Stille结合了以往所有大碟的特征,我觉得像是在列一张过往的清单一般。是这样的吗?
Tilo Wolff:部分是这样的。在Inferno里,我试图将Lacrimosa不成文的条条框框打破,之后,我觉得自己在之前说过的Stille状态中,所 以,为了在Stille中表现它,我需要放慢脚步,深思自己为什么会将做音乐放在第一位。我能够处理音乐使它精确地描述诗歌,除了使用音乐外,其他的方法 对于我来说并不是能够经常成功的。为此,Inferno就是必须的,它破除了所有一切无意义的、多余的东西,而这个过程使得Stille能够产生。在 Stille里我利用了所有Lacrimosa的储备,所有那些使我着迷的音乐视角,从而最大限度地揭示了歌词的特殊意义而不必考虑那些无聊的规则。
Q:Anne Nurmi在Inferno里只写了一首歌,而在Stille里则是整整两首。你觉得她将来会如何在你们的创作生涯中发挥作用?
Tilo Wolff:这个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的。虽然我们并没有故意这样安排过。也许她会在下一张大碟里写90%的歌词,当然,这取决于我们各自的独立工作以及我 们想要在下一张大碟里表达什么,这些都得看我们的追求的和谐程度。
Q:你和安妮是否仅只是专业上的朋友,还是有更亲密的关系呢?我的后一个推断有一部分是因为你们歌词簿里的照片。
Tilo Wolff:没错,我们相爱。
Q:这会给你们制作音乐增加障碍吗?
Tilo Wolff:我们的工作中并没有包括一起坐下来然后做音乐这样一个过程。在私生活中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多,所以这个过程是没有必要的。安妮写Not Every Pain Hurts的时候并不知道我的Stolzes Herz,我们并没有一起创作,但是她的歌曲却很自然地成了我的Stolzes Herz的延续。这种状况经常发生,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创作。我觉得,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高度集中的合作,就应该是由于我们内心有着密切的联 系,而前者,并不存在在我们身上。无论是从音乐、创作与对人类的看法等等角度上出发,安妮和我都有着相似之处,我们有过一些相同的经历,这些都成了我们关 系的基础,同时,这也是Lacrimosa逐渐变成了我们的二重奏的原因。
Q:你们有考虑过下一张大碟的方向吗?
Tilo Wolff:这个应该是自发形成的才对。起初,我对于Stille的设想与现在完成的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向。事情是这样的:你创作了音乐,然后你会发现自己 也对它很惊异。我从不会坐到钢琴前然后说:好,现在我要做一首摇滚乐了。歌词放在我面前就好象是张地图,或是个向导,这才是我的创作方式。当它完成的时 候,我时常也会很迷惑,因为我原本以为它会是富有侵略性的,或者是非常严肃的,但结果却完全不同。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做音乐的方式。当你让所谓的理性接管 了你的思想,你将不会为了单纯的"我想做一首好听的歌"这样的理由而感到满足,你会开始想怎样才能使它得到最好的推广与销售,要怎样做才能使它适合在电台 中播出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被毁掉,被流水线工业所替代。所以,我很高兴自己完全无法预测我的音乐的方向。